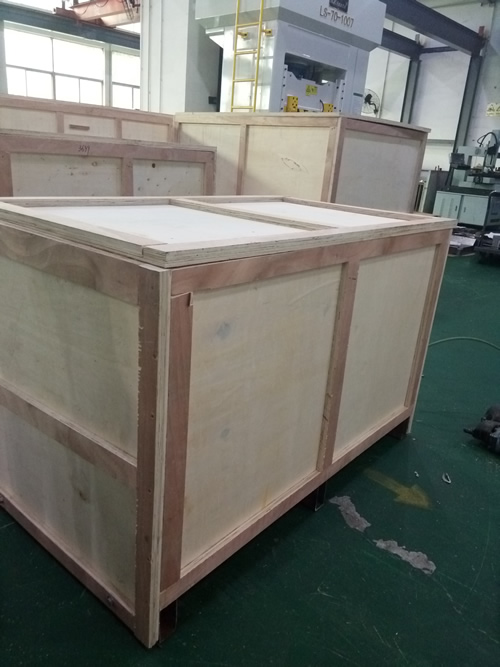“咱们离婚吧。”我将爱马仕包甩在沙发上,口气比谈判桌上的最后通牒还严寒。陈默端着排骨汤的手顿了顿,蒸汽含糊了他的黑框眼镜,连眼皮都没抬:“原因就这个?”
这平平的反诘完全激怒了我。我踩着十二厘米的高跟鞋,光着脚在大理石地板上踱步:“我现在是宏远集团的总监!今后要和上市公司老总对接,你呢?三十一岁还在破研究机构混日子,月薪六千连房贷零头都不行!”
陈默把汤碗悄悄放在餐桌上,汤汁溅起几滴。他摘下眼镜,用袖口渐渐擦洗:“你想要的日子,我给不了。”这句话像针,扎破了我一切假装的自豪。我吼着说要过“看得见未来”的日子,回身摔上卧室门时,听见他折腰擦地板的声响,轻得像叹气。

离婚协议签得反常顺畅。我自动多给他二十万,像在布施一只摇尾乞怜的狗。陈默盯着数字看了三秒,签字时笔迹规整,一笔一划都透着我从未读懂的沉稳。他的东西少得不幸:一个半旧的黑行李箱,几箱英文专业书,还有个装精细零件的木箱——他说那是“业余爱好”。
我在CBD租了月租八千的江景房,把意大利真皮沙发、北欧原木餐桌挨个搬进去。可每逢深夜回家,空荡的客厅里只要智能音箱的机械应对,才惊觉那些被我厌弃的“烟火气”,早成了习气。
三周后陈默打电话说要搬离,我正在新办公室挑装饰画,心猿意马地说“随意”。周六回去时,他正把叠得规整的白衬衫塞进箱子,阳光落在他鬓角,我第一次发现他有了青丝。阳台那个装零件的木箱不见了,书架上少了几本封面古拙的厚皮书。
“你那些褴褛都扔了?”我摸着新买的珍珠项链随口问。他把一件深灰色中山装叠好放进箱子——我从没见他穿过——“捐了,带不走。下周我去北京作业。”我讪笑作声:“你那破单位还能调去总部?”他没解说,仅仅说洗衣机坏了,记住叫人修。
升职后的日子像开了挂。我穿戴定制西装参与高端酒会,和宏达出资的陈总推杯换盏,听上市公司老总暗示“深度协作”。可团队老职工总说我浮躁,几个项目签了却落不了地。更奇怪的是,每次方针利好都精准砸在我头上,文件落款处总呈现“陈默”两个字。
我认为是重名,直到在中心方针研究室的官网看到简历:“陈默,1993年生,博士,专项变革组组长”。心脏像被攥住,我想起成婚时他爸爸妈妈说的“小默作业特别”,想起他深夜接的加密电话,想起书房里永久锁着的抽屉。那些被我当作“没出息”的依据,忽然有了令人窒息的解说。
三个月后,我以企业代表身份参与国家级职业研讨会,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。当主持人念出“中心方针研究室专项变革组组长陈默”时,我握下笔的手开端颤栗。
他走上主席台的瞬间,我如遭雷劈。深灰色中山装衬得他身姿挺立,金丝眼镜替代了旧黑框,从前沾着油渍的袖口此时平坦如镜。“当时职业最严峻的问题是立异断层,咱们拟定了三年变革规划...”他声响明晰有力,数据信手拈来,台下掌声雷动时,我才发现了自己泪如泉涌。
那些我获益的扶持方针,是他团队的效果;我讪笑他“无用”的专业书,是他深耕的范畴;乃至我能顺畅升职,都踩着他铺好的方针节拍。而我,曾用最尖刻的话,否定了他悉数的价值。
中场歇息时我躲在洗手间平复心境,出来却遇见他被一群人围住。部委领导拍着他的肩,企业总裁递上手刺,他站在中心沉着应对,和那个在家煲汤的缄默沉静男人判若鸿沟。“林总监?”他先看见了我,口气平平得像问好街坊。
“陈组长。”我结巴着开口,脸颊发烫。他递来一杯茶:“你们公司的项目我看过,技能很厚实。”没有责备,没有夸耀,只要真挚的必定。这时有人找他谈方针细节,他允许暗示后脱离,背影挺直得让我不敢直视。
回深圳后,我像被抽走了主心骨。寻求我的上市公司老总忽然被查,宏达出资的资金也没了下文。深夜加班时,办公楼只剩我一个人,保洁阿姨的清洁车轱辘声分外尖锐。我想起陈默临走前说的“洗衣机记住修”,才发现新公寓的洗衣机再贵,也煮不出那样暖的排骨汤。
春节前的政商联谊会设在人民大会堂,我穿戴赤色定制裙刚站稳,就听见有人说“陈组长年轻有为”。他站在不远处和老干部攀谈,深蓝色中山装衬得他气质沉稳,月光落在他眼角的细纹上,竟有些温顺。
银行行长热心地拉我曩昔介绍:“这位是宏远集团的林总监。”他转过身,目光平静地与我对视。握手时,我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松木香,和当年他煲汤时的滋味如出一辙。“曾经的街坊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解说,替我化解了一切为难。
联谊会结束时下雪了,他提出送我回酒店。奥迪A6的车厢里很安静,只要雨刷器刮雪的声响。“当年为啥不告诉我?”我总算问出那句憋了好久的话。他望着窗外:“作业性质不允许,并且那时你正神采飞扬,说了反而像夸耀。”
“我认为你真的没上进心。”我的声响发颤。“你寻求个人成功,我做国家工作,本就不同。”他回头看我,“你需求的日子,我给不了,不如放你自在。”车子停在酒店门口,我下车前说“我懊悔了”,他没答复,仅仅看着我走进大堂,目光里有我读不理解的杂乱。
回到深圳,我辞掉了总监职位,搬回南山区的老房子。找人修好那台洗衣机,从头买了他喜爱的原木家具,连沙发方位都摆得和曾经相同。我不再参与浮华的酒会,带领团队深耕技能,几个立异项目虽不挣钱,却让我找回了久别的结壮。
某天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看到他的报导,标题是《青年学者陈默:以方针之力赋能工业晋级》。相片里的他站在前,笑脸温文却坚决。我泡了杯他爱喝的龙井,渐渐读完文章,才理解咱们历来不是一个国际的人——他的战场在国家开展的蓝图上,而我曾困在个人得失的方寸间。
后来传闻他升任方针研究室副主任,常去各地调研。故土的朋友说,陈默春节回家时,爸爸妈妈提起我,他只说“各自安好”。我在阳台种上他喜爱的绿萝,看着远处的海岸线,总算想通:有些缘分错失不是惋惜,而是让咱们在各自的轨道上,活成更好的自己。
现在我带领团队拿下了国家级技能奖项,领奖台上,主持人念出支撑方针的拟定者时,我听见“陈默”两个字,安然地鼓着掌。散场后收到一条生疏短信,只要一句话:“洗衣机修好了,就好。”号码归属地是北京,我握着手机站在落日里,眼泪总算落下,却笑着删了信息。
这世上最清醒的生长,莫过于看清了别人的格式,也找准了自己的方位。他在庙堂之高护万家灯火,我在江湖之远守一方技能,如此,就是最好的结局。